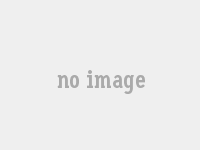这些年,随着血管介入技术和工程的迅猛发展,支架、人工血管与组织工程不断拓宽着血管治疗的边界。
在这样的语境下,时常会听到一种观点:“血管狭窄都能放支架了,大隐静脉也没有必要留着。”
然而,从血管外科与血流动力学的视角来看,这样的结论有其明显局限:
首先自体静脉作为桥血管移植物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其次这种观点忽略了大隐静脉作为人体器官的长期价值。
【温馨提示】本文仅用于提供科普专业信息,不能替代专业医生的诊断与治疗。建议患者根据自身情况咨询专业医生以获得个性化的治疗建议。如需预约线下张强医生集团静脉曲张CHIVA中心门诊,请通过公众号“张强医疗科技”自助预约北京、上海、成都、深圳、济南连锁中心看诊。
在欧洲,CHIVA创始人Franceschi 教授长期倡导:大隐静脉作为人体器官的角色不应被忽略,它不仅仅是一段可以随时被“切除、闭合、硬化、烧灼”的血管。
在他的著作与文章中,多次提出这样一个基本立场:只要这条静脉仍然具有潜在价值,在任何破坏其结构之前,医生就有责任让患者知道——它可以被保留,也存在保留的治疗路径。

这首先是一个权利问题,而不仅仅是“技术路线怎么选”的问题。而我们今天就从伦理角度谈谈大隐静脉的去与留。
01
从静脉外科的发展回望:
大隐静脉从来不只是“能不能拿来搭桥”
在血流动力学尚未普及的年代,面对下肢静脉曲张,外科医生更多是从“形态”出发去解决问题。
剥脱、腔内消融、硬化等祛除性治疗之所以迅速流行,是因为它们直观、快捷,能在短期内明显缓解症状、改善外观。
从当时的技术条件和知识背景来看,这些治疗并无不妥。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我们的视角发生了改变——
- 血流动力学的知识不断积累和体系的成熟
- CHIVA 理念在国际上被反复验证和讨论
- “保留结构、恢复功能”在多学科外科中成为新趋势
在这样的背景下,大隐静脉逐渐回归本位:
它不再是一条只能废除的“功能不全的静脉干”,
而是一个拥有被保留机会、长期参与静脉引流、具备结构功能与未来可能医疗价值的器官。

正如 Franceschi 在关于“保留大隐静脉伦理与依据”的社论中所强调的:在决定破坏之前,必须意识到这条静脉的潜在价值,包括但不限于移植物,也包括它在静脉网络中的生理角色。
02
Franceschi 所强调的核心:
不可逆损失之前患者应拥有真正的知情与选择权利
Franceschi 的观点,并不是简单地说“所有人都要保留大隐静脉以备将来搭桥”。
他的关注点更为基础,也更为普适:器官的不可逆损失,必须建立在充分知情和真实选择之上。
1. 大隐静脉:不是“管子”,而是有功能、有适应性的器官
在他关于盆腔与下肢静脉血流动力学的论著中,Franceschi 多次将大隐静脉视作一种“珍贵材料”,强调它在各种情况下可能成为必要资源,应在决策前明确告知患者其潜在用途与意义。
他强调的并不只是“移植物价值”,而是几个层面:
它参与浅静脉向深静脉的引流,是局部血流调节的一部分
它具备活体组织的修复与重塑能力,可以适应不同压力环境
即便当前存在返流,只要流路被纠正,静脉本身往往仍有机会恢复功能
换句话说,大隐静脉并非“坏了就扔”的结构,而是一个在功能失衡中“被连带受累”的器官。

2. 去除器官前,知情权不是形式,而是边界
在一篇专门讨论“保留大隐静脉的伦理与依据”的社论中,Franceschi 直接提出:
在考虑剥脱、消融或闭合之前,必须向患者说明两件事:
存在保留大隐静脉的治疗路径(例如 CHIVA 等保守血流动力学方案);
一旦大隐静脉被破坏,其结构和潜在用途属于不可逆损失。
在面向患者的教育平台中,这一点被表达得更加直白:
知情同意书中应当明确说明:大隐静脉是可以被保留下来的,并且在未来某些场景下可能被用于重要手术;而 CHIVA 等保留方案在长期随访中并不逊于甚至优于某些破坏性治疗。
这背后的逻辑很简单:
器官一旦被去除,患者失去的不仅是当前的静脉段,还有未来所有的可能性;
医生无权在患者不知情的前提下,替他做出这样一个“永久决定”;
尤其是目前医学已经具备了保留器官的能力之后。
因此,伦理义务不在于“替患者选好”,而在于“让患者真正理解自己在做什么选择”。

3. “解剖资本 / 静脉资本”的概念
在后续的一些讨论和研究中,“大隐静脉作为静脉资本(venous capital、anatomical capital)”的概念被反复提及——
意思是:这是患者仅有的一部分解剖资源,一旦消耗不可重建,应当尽可能在科学前提下节约使用。
这并不是要夸大它的用途,而是提醒临床医生:
在具备保留方案的前提下,把大隐静脉简单视作“可以随手处理掉的多余结构”,在伦理上是站不住脚的。
03
现代血流动力学给我们的启示:
切除,不再是理所当然的终点
血流动力学带来的最大改变之一,是让我们重新理解“曲张静脉”这件事。
在严谨的描记和分流分析之下,我们越来越清晰地看到:
曲张静脉团块,并不是病因本身,而往往是长期湍流与压强失衡的结果;
真正需要干预的是异常返流的起点(EP)、异常路径以及压力传导,而非简单的“把看得见的静脉全部去掉”;
许多静脉在流路被纠正后,完全有机会回到相对生理的工作状态。
在这样的前提下,“保留大隐静脉”不再是一种理想化的呼吁,而是一条可操作、可验证的临床路径。
CHIVA 及其变式在长期随访中的研究已经表明:在合适的适应证和规范操作下:
症状缓解与复发率不逊于、甚至优于传统剥脱PMC
皮下神经损伤、瘀斑等并发症发生率更低
最重要的是:大隐静脉及其解剖资本得以保留,为未来留下余地
这使得“切除”从一个默认选项,变成了需要经过权衡后才使用的手段——
它仍有位置,但不再是唯一答案。
伦理责任的重心:
不是夸大用途,而是尊重未来的不确定性
在讨论大隐静脉的去与留时,最容易出现的,是两种过度简化的说法:
“每个人都需要保留静脉用来做移植”——这并不符合事实;
“大隐静脉以后一定用不上”——这同样缺乏依据。
成熟的医学伦理,强调的不是“预测未来”,而是承认未来的不确定性,并在此基础上尊重患者的选择。
因此,真正的重点在于:
1. 医生不能替患者“关掉一扇门”
以当前的知识水平,我们无法精准预测每一个患者未来二十年的心血管风险、动脉病变进程或其它疾病演变。
既然大隐静脉是不可再生的器官,在有保留路径的前提下,轻易去除,等于替患者提前关掉了一扇可能有用的门。
2. 不可逆损失之前,知情同意必须“实质化”
有相当一部分文献与倡议已经明确提出:在涉及大隐静脉剥脱、消融或闭合前,应向患者说明:
这条静脉可以不被破坏(至少在一部分情况下可以);
保留方案(如 CHIVA)在长期疗效上已有证据支持;
一旦去除,这条静脉将永久失去,无论未来是否需要,都不再有重新“找回”的机会。
只有在这样的信息前提下,患者的签字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选择”。
3. 保留,并不等于牺牲当下的治疗质量
有了血流动力学支撑与成熟的保留技术,伦理不再是“理想主义”,而是很具体的临床实践路径:
在相当多的静脉曲张患者中,既可以获得满意的症状改善,又可以避免对大隐静脉的彻底破坏。
这意味着:“尊重未来可能性”不再是一种“与疗效对立的道德要求”,而是一种可以被实现的专业选择。
04
结语:
医学的成熟,是在克制中获得的清醒
回顾外科的发展,很多学科都经历了从“切得更多”到“保留更多”的转变:
- 乳腺外科从激进性切除走向乳腺保留
- 胃肠外科从单纯追求切除范围,转向功能保留
- 肝脏外科从大块切除走向精准切除与剩余功能保护
静脉外科也正在经历类似的阶段。
在是否去除大隐静脉这件事上,我们真正需要的,不是立场的对抗,而是一种面向未来的医学责任感——
- 不否定既往技术的历史贡献;
- 不与介入手段“对立”;
- 而是在已有证据与技术条件下,尽可能减少对人体器官的不必要破坏。
保护大隐静脉,并不是因为所有人都一定会用到它,
而是因为它本身是一段值得被尊重的器官,是患者身体的一部分解剖资本。
在腔内时代,在技术快速迭代的今天,
也许我们更需要的是这样一种清醒:
@
有保留能力的今天我们可以多想一步
在可以选择不破坏的时候,
尽量保留;
在必须做出不可逆决定之前,
一定讲清楚。
这大概就是血流动力学时代,静脉外科所能达到的一种伦理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