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十月十日是世界精神卫生日。“今天我又emo了”“玉玉症”“蕉绿”“蓝瘦香菇”“网抑云”……这些说出来大家都懂的话语,从网络走到现实有十几个年头了。缩略词和谐音字所表达的抑郁,记录了无数网民的精神生活状态,也诉说着“抑郁症”作为一种精神疾病与社会发展的相关性。从近几年的图书畅销榜单与社交平台热帖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当下人们对抑郁等相关心理话题的关注。但抑郁症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抑郁症在当代社会逐渐成为了流行病?当我们谈论抑郁症的时候,我们谈论的究竟是什么呢?
法国社会学家阿兰·埃伦贝格的《疲于做自己:抑郁症与社会》抽丝剥茧地为我们分析了“抑郁症”这一精神病学概念的流变,从而展现出整个当代社会对人的理解和主体性本身遭遇的变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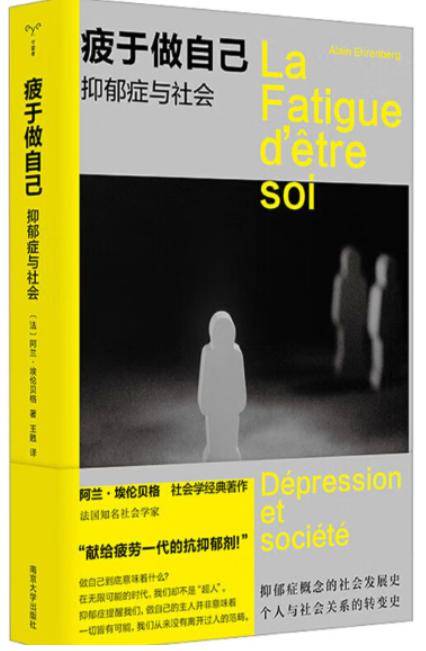
《疲于做自己:抑郁症与社会》(法)阿兰·埃伦贝格 南京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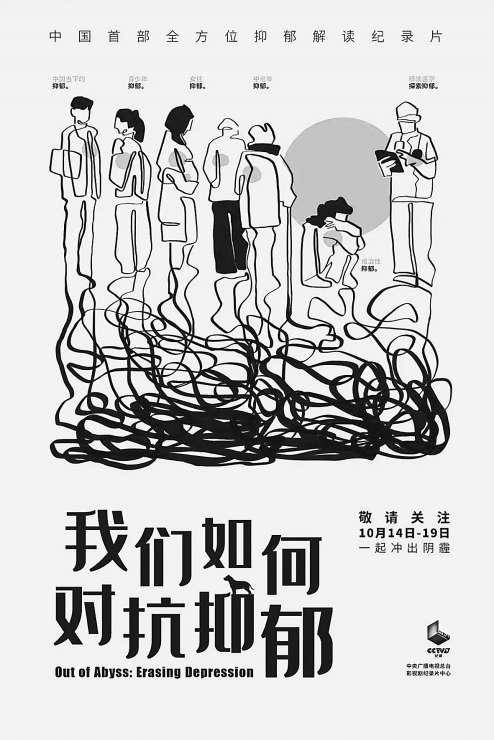
2021年播出的我国首部关于抑郁症的纪录片《我们如何对抗抑郁》海报
医学和社会的纷争
抑郁症的核心外面有厚厚的胞衣,它与为何做自己息息相关,埃伦贝格在前言中阐述了自己的三段论:个人如何走向身份认同和社会成功、征服的理念如何让精神问题受到关注、当代人轮廓如何被勾勒。这看起来和一般的社会学著作别无两样,然而在后续的不断细致剖析中,作者似乎有意用一种更为繁琐的方式,阐述精神病学的种种概念,将文字作为镊子,仔细扒开层层胞衣,让抑郁症逐渐显现,让社会标准的演变露出牙齿。
主体必然是最重要的关键词,这恰恰又是最难辨别的。“疯癫”这个笼统的精神疾病表征在19世纪末开始有了具体的分类,这种对类型的划分有助于医者更快捷地对病患入手,可是,疾病的临床实践和生物研究还在遵循着希波克拉底的指示——揭示疾病的本质。在进入20世纪前,与精神疾病相关的各学科就一直在争夺,看似争夺的是主体:疯癫本身、具有痛苦的实体、能够吐出可被理解话语的病人……然而被目的所掩盖的是各家方法的比武,是弗洛伊德式冲突论和雅内式匮乏论的此消彼长,是英美实用主义对阵法国形而上思考,是各类药物对病患和市场的争夺,“人们不再区分什么是治疗,什么是嗑药。在一个不断服用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的精神活性物质以追求情绪改善的社会中,人们不再知道自己是谁,甚至不再知道谁才算正常。”
在论及精神病学的特殊性时,主体成了精神病学本身,埃伦贝格无时无刻不在陈述精神疾病的症状:创伤、疲劳、神经衰弱、歇斯底里……甚至延伸到综合征和新病名,虽然看似精神病的范围在扩大,但在技术进步的同时,医药学和心理学逐渐结合,精神疾病的复杂性好像是一种巨大细胞生物的内部分裂。而弗洛伊德最终将精神疾病的主体铆钉在病人这里,有了患病主体,诊断、病因学和治疗才能够围绕其旋转起来。
可主体依然总是遁入晦暗,越发大放异彩的是治疗方法。普通科医生给出的药物疗法让精神分析疗法一直屈居二线行列,毕竟,能够快速高效解决身体上的痛苦,让人立即回归“正常生活”才是最要紧的。而电击休克疗法以及麻醉药物的实验性方法,在如今看来无外乎是一种极端的暴力,参与其中的无论病患还是治疗者,都已经放弃了对主体的尊重,治愈,才是他们迷恋的目标。精神疾病带来的痛苦,用痛苦的方法来治疗,披着神经症外衣的抑郁症并没有因此变得越发清晰,而是被电流击打成了多种样貌的神经性抑郁和忧郁性抑郁。
按照一贯的方法,分类越详细,就越能有效地针对治疗。医药学在几十年间不甘示弱地发明出神经安定剂、抗焦虑药物和抗抑郁药物,相较于让人昏睡的镇静剂或是让人产生愉悦感的兴奋剂,这些药看起来优秀太多,却有很大的成瘾风险。不仅是精神病学家,医药公司和外科医生们也深入药品的研发。几十年间无数繁杂的术语描述着难以定义的新鲜事物,各种药剂、以有机杂环化合物(嗪)为名称结尾的三环类药物、合成酶的使用……一时间精神药理学成为了大家都感兴趣的领域,化学家、药理学家、生理学家、普通科医生、心理学家、社会学家都想为改变人类行为出一份力。主体没有因为抑郁症的语言和表现变得独立且具有自主性,反倒被扯进了社会与科学的纷争。
抑郁症与现代性
抑郁症是怎样产生的?或者更精确点说,是怎样被发现的?这种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的“忧郁”的表征,在宗教统治时期被看作是恶魔附身,到了18世纪又被转化为“理智”受损,因为“精神”逐渐显形。到了19世纪,才有了进步式的发展。从歇斯底里到神经症,再到“心灵的感冒”,抑郁症时而被妖魔化,时而又被轻描淡写。在20世纪后半期的欧美社会,抑郁症好像迎来了大爆发,仅1978年医生们就开出了500万张抗抑郁药的处方。如今的中国媒体上也经常有文章描述当下社会的抑郁症患者生存案例。埃伦伯格在医药学和病理学的发展中,也不断提醒着我们造成这种结果的社会原因。
自19世纪最后20年起,工业化和大城市将现代社会推到了人们面前,没有了宗教的规训和帝王的榜样,人需要拼尽全力来思考,以追上这世界的脚步。登上现代主义舞台的作家和艺术家以神经质、感觉和本能为灵感,描摹着现代人的当下状态。然而打破旧的规范后,人获得的自由却让人走进了另一种困境,激发出了人对自我身份的怀疑,从而感到焦虑不安。社会影响着人的神经系统,抑郁症表现为了一种责任感的疾病,患者不能胜任负担自己生命的工作,他们感到疲劳、疲惫甚至无望,他们厌倦做自己。
普通医学无法对这种社会普遍症状给出答案或理论基础,自由带来的某种“主观能动性”让自我分析成为风潮,自我言说的泛滥引发了危害公序良俗的公共问题。于是社会站到了个人的对立面,为了保障秩序而重新制定了框架:“身体必须是顺从的,家庭必须是值得尊敬的,野心必须是适度的。”这期间,文学作品、期刊杂志和大众媒体频繁强调着,抑郁症也可能发生在拥有健康生活的人身上,抑郁既不是精神疾病,也不是虚构故事。
上世纪60年代开始,精神分析开始在精神病学中占据重要位置,法国人崇尚的形而上思考也以文学和哲学的形式走入其中,海德格尔启发了精神病学家,拉康更是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精神分析学家朱莉娅·克里斯蒂娃以自身经历为样本,用艺术与文学的疗愈之法来抚慰个体遭受折磨、无法被言说的痛苦状态。然而埃伦贝格却没有从单一方面入手,他环顾四周,进行着全方位的考量——克里斯蒂娃所谓的“悲伤是抑郁症的基本情绪”,主要针对的是症状单一的患者,反倒是大众刊物给出了一种内心生活的语法。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女性杂志,从最开始耸人听闻的“灵魂癌症”,到《神经抑郁症波及所有社会阶层:勤劳的人、懒散的人、穷人、富人》,《她》和《玛丽-克莱尔》两份重要刊物以严肃又不乏幽默的语调来让人们关注自己的生活,思考自己的精神冲突。
美国的“迷惘一代”和“垮掉一代”文学虽然充满了创伤与不修边幅,但威廉·巴勒斯的《瘾君子》还是将苦闷、不羁与恐惧同时呈现在世人面前。文字与媒介给了人新的公共空间,让个体面对需要自己来制定新规范的社会,拥有表达自己的语言,这不仅减少了人们在谈论个人问题时的羞耻感和内疚感,也给予了个人叙事一种社会合法性。文化,或许是对抗抑郁症的一种防御机制。
我们需要理解复杂
埃伦贝格的这本书充满了不确定性——“没有什么被真正禁止,没有什么是真正可能的”“无法定义”“诊断混乱”……还有无数的问句,统统构成了抑郁症复杂的历史与概念。争论仍在继续,新的观点继续层出不穷,抑郁症中抑制与冲动的两个维度既互为反面又对立统一。抗抑郁药物百忧解(prozac)成了一时的赢家,也代表着苦痛占据着社会的中心位置,作者最终不得不承认,虽然一切皆可治疗,但是精神疾病的不可治愈,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抑郁症是一种媒介,是一个十字路口,它是一个关键部分,代表着一种社会期待。埃伦伯格最后还是倾向于将这种精神慢性病的轮廓归类于形而上,既然疾病靠各种症状的表征来显形,那就从治疗的角度来看待疾病。在治疗的过程中,人被不断塑造,抑郁症的历史更多的是对人的类型的塑造史,它是在精神自由和个人能动性的双重要求下形成的。“抑郁症是历史中介,它令受到神经症威胁的冲突的个人退出,让位给融合的个人,新的个人为了克服持续的不安感而上下求索。匮乏被填充,淡漠受到刺激,冲突被调节,强迫被克服,这一切所导致的依赖构成了抑郁症的另一面。”
抑郁症在不同社会中,还在根据形势继续发生变化,精神病学的新局面让患者在治疗和药物的影响下成为全新的个人。作者埃伦贝格所塑造的抑郁症历史,是学科的融会贯通以及立场间的较量,是社会进步对个体造成的难以挽回的影响。在他近乎完全依靠数据的客观阐述中,弗洛伊德、雅内、拉康,甚至尼采都成为了精神疾病学科的理论依据。严谨客观的分析或许缺少了某种对于病患的共情,甚至在参考大众杂志时还保留一些对女性的刻板印象,但埃伦贝格的视角依然呈现了更为立体、丰满的抑郁症形象。他的书写好比游乐园里的碰碰车,虽然各种说法横冲直撞,历史脉络横竖交错,但并没有脱离开现代社会发展范畴的精神病学。他没有对抑郁症妄下结论,这既呈现出一种缜密,也为了避免阅读者会套用概念来诊断自己或者诊断他人;他对药品的详细说明,是医生对问诊者的耐心讲解,也含有从医者告诫大众“是药三分毒”的善意。
埃伦伯格用冷冽的科学声调告诉这个看似进步实则满是孔洞的社会,抑郁症既是一种时间病,也是一种动力病,它意味着责任要被承担,疾病也需要被治疗。缺陷与冲动是一体两面,不要拘泥于僵化的看法,心灵的症结是每个人都会有的。我们最终要理解的,是复杂与互融。
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 张序





